婉拒唱歌的句子说说(婉拒唱歌的句子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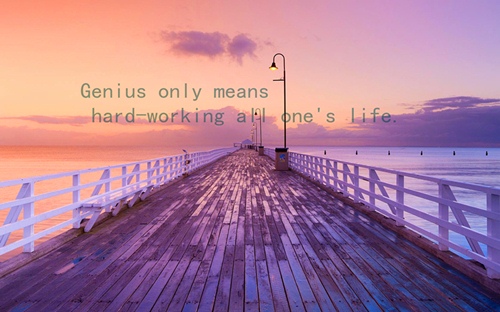
”感君千金意,惭无倾城色“,教你如何婉拒他人,不做冤大头
\r\r\r\r\r 陌上花开\r \r \r \r/**/\r \r\r\r\r 感君千金意,惭无倾城色\r\r (上)\r\r这句话,我很想对别人说一说。苦于一直没有男人赠予千金或是价值千金的东西,所以我也就一直没有机会做出羞答答的样子说:“感君千金意,惭无倾城色。”
\r\r一个女人,以色事人固然是很卑微的事情,可是如果不能够以色动人,同样是很卑微的事,会郁闷到内伤。大多数人都想这样吧,他为我倾倒,而我又不对他迷恋,姿态潇洒,态度游离。
\r\r这两句很撩人的话,出自《碧玉歌》。《乐府诗集》里共录《碧玉歌》六首,有题为孙绰作的,有题为梁武帝萧衍作的,还有唐朝的李暇作的,虽然作者很不统一,但风格和内容都很接近,都是以碧玉起意,以碧玉为歌。
\r\r书上说,碧玉是宋汝南王小妾,汝南王宠爱她,就为她作歌。但是宋无汝南王,疑为晋汝南王之误。晋汝南王叫司马义。他有一个小妾叫碧玉。碧玉姓刘,她并不美艳,但从汝南王对她的宠爱来看,她应该颇有媚态,很吸引男人,而且歌唱得很好,虽然她自谦说“惭无倾城色”,但是女人谦虚的话多是不能相信的,她们通常是为了引出更多的赞美。(男士切记!)
\r\r我把六首碧玉歌都摘录出来,从中读出一个少女的成长和成熟。
\r\r碧玉破瓜时,郎为情颠倒。芙蓉陵霜荣,秋容故尚好。\r 碧玉小家女,不敢攀贵德。感郎千金意,惭无倾城色。\r 碧玉小家女,不敢贵德攀。感郎意气重,遂得结金兰。\r 碧玉破瓜时,相为情颠倒。感郎不羞郎,回身就郎抱。
\r\r——晋•孙绰
\r\r杏梁日始照,蕙席欢未极。碧玉奉金杯,渌酒助花色。
\r\r——梁•萧衍
\r\r碧玉上宫妓,出入千花林。珠被玳瑁床,感郎情意深。
\r\r——唐•李暇
\r\r梁武帝和李暇的,艳丽妩媚,为歌而歌,折损了活泼真切的情感,所以读起来漂亮而不生动,我们不去谈它。感觉上越往后的朝代诗文越是有这样的毛病,诗经、唐诗、宋词即使作艳语也有朴素生动的味道,我们读到,就好像亲见当时情景,感知到当中蓬勃的情意,就像我们读李白的诗,看到他在山间高臣卜,在花下独酌,知道他的落寞和豪放,与他同喜同悲。柳永的词也艳,“衣带渐宽终不悔,为伊消得人憔悴”可谓至艳的情语,但没有人觉得它浮靡,不堪咀嚼。
\r\r及至《碧玉歌》也是。《碧玉歌》是情歌,魏晋文风所致自然也艳到不堪。像“碧玉破瓜时,相为情颠倒。感郎不羞郎,回身就郎抱”,简直就是破到艳情,直白大胆之处和《花间集》中描写男女欢爱的词不相上下。
\r\r“破瓜”,我在看古典小说时经常看到。现在,这个词已经被人误传到有点的味道。想必老师上课说到这个词也大为头疼,因为不说,学生不能真正地理解意思。说得不好,又有误导下一代的意思。破瓜是指女孩十六岁,俗话说的年方二八。篆字“瓜”很像两个“八”字叠在一起。所以古人常以“破瓜”指女子二八年华。
\r\r碧玉到了十六岁的时候,处子的清香开始散发,弥漫。她偶尔秀发微拂,露出圆润小巧的耳垂,白皙修长的颈脖,她步态摇曳,行走也带着香气,回眸一笑令人心醉神迷。汝南王要求和她欢好,也就是正式将她纳为自己的姬妾。这一首就是写他们欢爱之时的情景。诗以碧玉的口气说,现在我到了十六岁,已经懂得了您对我的情意,与您一样,我也为我们之间的情意心意缱绻,不再因为您对我表示好感而感到羞涩,我不再逃避您,而是转过身让您抱住我,接受您的爱意。
\r\r孙绰作的《碧玉歌》四首,据说是应汝南王司马义的邀请所作,歌以碧玉的口气,诉说了他们感情的发展和深入。歌中所唱的碧玉小家女,是我们常说的“小家碧玉”的由来。碧玉门第不高,故自称小家女,称汝南王为“贵德”,我喜欢看他们之间的恩爱互酬,女的谦逊,男的宽大。像天空和飞鸟之间,他有为博一笑倾千金的疏豪,她有感君千金意的喜悦,像飞鸟一样从容地掠过广阔天空。
\r\r越来越懂得,情感的交付是平等的。真正的感情不因地位、权势、尘世间的种种动荡而改变,也不去谴责男尊女卑的观念,一夫多妻的制度。因为如果以傲然姿态凌人的人,注定得不到人的真心尊重,因为人家不过是一时弱小,臣服在你脚下,有朝一日当她强大起来,会以同样的姿态对待你。一夫多妻或拈花惹草的男子也一样,他们将爱分散了,妄想着别人雨露均沾时会对他念念不忘,其实不过自欺欺人。为什么?你不给予我全部的爱,却要求我全心以对?士为知己者死。如果你对我是真心的,我会以同等郑重的感情来回报你。
\r\r就像汝南王对待碧玉一样疼惜。碧玉了解了他的爱意后,怎可能不全心回报?
\r\r (下)\r\r想到汉乐府里,有一首《羽林郎》。同样是很有名的,只是偶尔被《陌上桑》的名声掩盖。它是东汉的辛延年有感于权贵豪强随意欺凌妇女这一社会现象所作。《羽林郎》里的胡姬,是非常有胆色的女子,她年方十五六岁,已经当垆卖酒了。卓文君也当垆卖酒,但年纪一定大过她,而且有司马相如陪着,不像胡姬孤军奋战。
\r\r汉朝的时候,匈奴等外族已与汉朝通商,洛阳长安等地常有胡人来经商。胡姬是外族的女子,但胡姬给我的感觉总是亲近,总觉得哪里见过,后来想起来她和古龙《萧十一郎》里面的风四娘一样,都像曼陀罗花那样艳辣撩拨,风情万种。
\r\r因为是讽刺诗,辛延年用了托言的手法,他假托这个调戏民女的豪奴是霍家奴。霍家,指西汉的大将军霍光,霍光当年权倾朝野,整个家族人都官居高位,女儿也入宫当了皇后。霍光死后,妻子郭氏指使人毒死先皇后许平君的事情暴露,汉宣帝刘病已为妻报仇,清算总账,诛了霍家九族。
\r\r虽然不是霍光,这个人也是一个权贵的家奴,他依仗主人的势力横行霸道。在杨贵妃最得宠的时候,杨国忠的家奴冒犯了公主的车驾,驸马和他们理论,他们干脆连驸马也痛殴一顿。可见这些豪奴狗仗人势到了什么地步。
\r\r冯子都这个奴才骑着马招摇过市,无意间看见了胡姬,看上了胡姬的美色就上前调戏。一看胡姬本身打扮得很时尚,又是当垆卖酒的,就以为人家很随意,会任他轻薄,他在店里先是要酒,后是要菜,然后又轻浮地想把青铜镜系在胡姬胸前的衣襟上。谁知胡姬的胆色非一般的娇弱闺秀可比,她一一满足他的要求,面对他的调笑,待之以礼,晓之以情,最终表明态度,宁死不从,让豪奴无可奈何。
\r\r“多谢金吾子,私爱何区区”和碧玉说的“感君千金意,惭无倾城色”是一样的意思,不一样的是,胡姬是看似礼貌的断然真拒,而碧玉说这话则是情人之间耍花腔的假拒。
\r\r我非常欣赏胡姬说的几句话,几乎可以看见她说这几句话时的庄重神态:“不惜红罗裂,何论轻贱躯。男儿爱后妇,女子重前夫。人生有新旧,贵贱不相逾。”
\r\r其实想清楚了,就会发现人除了生死之外无大事,若我们的胆色,对事态的判断及把握已经跨越了生死,那就再没有力量能约束我们。就像秦王奈何不了蔺相如,冯子都也无法控制胡姬。
\r\r我可以撕裂这罗裙,不惜这性命。因为我心中有信念,我有自己珍重的情感。我有想要珍惜的人,不是你凭借外力可以横加干扰的。
\r\r对自我的坚持和肯定,胜过一切外在的虚名荣誉。“人生有新旧,贵贱不相逾”一句是最令我震撼、铭心不忘的。人,真的很难做到不喜新厌旧。通常能够喜新不厌旧就是很难得了,而真正能明白自己的身份处境,不因贫贱而羞惭,不因贫贱而焦躁,安贫乐道就更难得。
\r\r多数时候,人都是想竭力往上攀爬的,镜花水月心思虚妄。所以你看见《古诗十九首》记下了寒门士子在世族门阀制度的压制下那么多的不平和悲愤。但在一个胡姬的口里(在辛延年这样默默无名的人口中),说出的竟是这样平淡有力的话。
\r\r还是乐府里的《古艳歌》说得好:“茕茕白兔,东走西顾。衣不如新,人不如故。”
\r\r\r试分析莫言拒绝唱赞歌的真正原因
如果说,文学负有使命,那么它的使命到底是什么?唱赞歌?暴露、批判?还是两者兼之?
自从文学诞生以来,海量的事实告诉我们,在不同的阶级范畴内,文学作品既可以唱赞歌,也可以暴露与批判(关于这一点,很多网友都写过此类文章,举过大量的例子,因此,笔者在此不再赘述了),关键就在于作者站在什么样的阶级立场上,具有什么样的思想倾向,他爱的是什么,恨的又是什么。
在浩瀚的中外文学史上,从不曾发生过有关文学功能的争论,历史上所有的作家、诗人们,无不都是当歌则歌,当批则批。对此,从未有人觉得这有什么问题。
唯一提出有问题的,是当今中国的模仿派魔幻作家莫言。他全盘否定了唱赞歌,把唱赞歌说得十恶不赦,而把暴露与批判奉作圭臬。
其实,莫言所论是文学史上一个最大的悖论,一个伪命题,所以,为此争论显得毫无意义。
莫言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悖论?难道是他天才地发现了文学的真谛?而在他之前的所有文学人都是笨蛋,愚不可及?非也!莫言之所以一棒子打死唱赞歌,而独尊暴露与批判,,纯粹是出于他的一己之私。
什么是莫言的一己之私?他的一己之私就是,他不欲为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,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唱赞歌。
他为什么不欲唱赞歌?
因为他内心深处不存在对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一切的丝毫的爱意(有的只是满腹的怨与恨)。
没有爱,就不会有感动;没有感动,就不可能唱赞歌(而怨恨总要找机会发泄出来的)。
生活经验告诉我们,倘若一个人对某某人或某某事心中有爱,心中有喜,一旦情到深处,他就会情不自禁地把赞歌唱出来,它有如泉水涌出泉眼一样自然、流畅。他的爱越深刻,越炽热,他唱出来的赞歌就越真挚,越响亮,越奔放,越动人。
在中国这片英雄辈出的土地上,从不缺乏应歌当歌之人、之事,缺乏的是作家心中的爱,和对高尚的崇敬。
莫言就是。
在莫言的眼里,这片土地上全都是“比鬼还可怕”的坏人——除了他的母亲。
当然,说莫言没有爱也不尽然。他深深地爱着他的母亲(他对他的女儿一定也是爱的,因为他说过,他只对生他的和他生的人负责),以至无论他走到哪里,就把给他母亲的赞歌唱到哪里,一直唱到了诺文奖的颁奖现场。
还能成为佐证的,是他对日本人(尤其是北海道的日本人)的爱。他不仅在他的一系列小说中始终没忘记对日本鬼子赞之歌之,而且还专门写了一篇《北海道的人》,对日本人大唱颂歌,唱得情真意切,行云流水,岁月流逝,仍彰显出他对于日本人长情可鉴。
这难道还不够说明一切吗?
文学该不该唱赞歌,这不取决于文学本身,而是取决于作家的阶级立场和政治倾向,取决于心怀什么样的爱,爱什么。
最后,笔者想吐出一个如鲠在喉的疑问:莫言无疑是不爱党的,根据是他从未为伟大的中国唱过半句赞歌,而且总是把党说得一无是处,着实可恨,既然如此,那他又为何要加入中国呢?